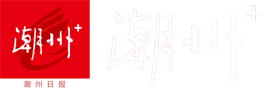二、潮州古代文学之滥觞
以文字为工具的古代潮州文学之出现及其滥觞,应在中原移民南迁入潮,中原文化融入潮州之后。根据史料考察,秦统一岭南之后,中原移民逐渐南迁入潮。“三国战乱,特别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又续之以永嘉之乱,中原战祸连年,导致大批移民南迁,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辗转进入本区,致使本区人口有大幅度的增加。”随着中原移民之南迁入潮,中原文化也随之融入潮州。隋唐以后,潮州郡级政区建立,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边远潮州地区的控制,不断派遣官员入潮,如张玄素、唐临、常衮、郑余庆、韩愈、李宗闵、李德裕等。这些官员多为朝廷贬官,“贬官南来对于他们自身是磨难、不幸,而对于潮州无疑是一桩好事:贬官是儒家文化打造的产品,多是饱学之士,从文化心理上说,他们来到潮州这样一个在当时文化教育依然十分落后的偏远之区,不满现状,进而要求改变并付诸自己的施政是可以预料的。”他们兴学教士,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使中原正统的儒家思想和理念逐渐融入潮州地区。正如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始潮人未知学,公(韩愈)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今号称易治。”同时,据郑群辉教授之推断,南朝刘宋年间,佛教开始传入潮州。
佛教的传入,首先必须要有传教的人,有信众,有一定的宗教氛围,一定的物质条件,尔后才可能有佛教寺院。有史可稽者,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被贬为潮州刺史的礼部尚书唐临,便是一个佛教信徒,且著有《冥报记》一书,以宣扬佛教因果报应、扬善戒恶之说。唐临莅潮四年,并死于任上,当以其佛教信仰传播潮州。潮州在其感染与传播之下,自然便有了佛教的信众。更为可贵的是,唐大历初年(766-779),潮州便已出现了西山惠照、药山惟严和宝通大颠等几位在全国都十分出名的得道高僧。“惠照者,本邑人。高僧大颠之师而曹溪之脉也。唐大历初归自曹溪,深契南宗之旨。”“药山释曰惟俨者,亦以童年妙悟,度岭入潮,与大颠共受心印于惠照。”“大颠,俗姓陈氏(一曰姓杨),世为颍川人。开元末产于潮,生而灵异,龆岁即遁栖云林,超然物外。大历中,与药山惟俨并事惠照禅师于西山之阳。”可见,唐代潮州虽然地处偏远,经济文化落后,但佛教在潮州的传播起点却甚高,就以上列举佛教僧人,都是当时在国内佛教界独领风骚的南宗禅之嫡系高僧。从大颠“门人传法者”便“众至千余人”,可见他们在潮州的传教已有不小之规模。
潮州佛教寺院的创建,有史料可寻者最迟始于唐初。元代释大訢《南山寺记》载:“寺建成于唐初,始未有业产。开元二十二年(734),有揭阳冯氏女,以父母卒,无他昆季,终丧,持田券归于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潮州开元寺原住持慧原法师编著的《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则说:“我潮开元寺,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敕建者。然据寺内耆耋相传,谓寺前身为‘荔峰寺’,则之佛教于唐开元之前已有之矣。”还有一些尚待考证的史料可供参考,如称建于晋代的饶平信宁都黄芒山(今海山镇)隆福寺,称建于“唐正观(贞观)六年”的潮阳竹山岭莲花院,以及相传建于晋朝年间(265-420)的潮阳西岩(或称海潮岩)等。这些史料证明,佛教在潮州的传入,当在唐代之前,郑群辉教授的推断是较为公允的。因为佛教之传入当在有史料记载的传教之人和寺院创建之前。
由是,独具特色的潮人文化得以在中原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长期浸润之下逐渐形成。也因此,饶宗颐教授认为,潮人文化源头存在着一种儒佛交辉的态势。而这种文化土壤,正是潮州古代文学赖于滋长之文化温床。
然而,文学的滋生与成长,除了文化的浸润之外,尚须借助一定的经济发展。潮州地处偏远,开发较晚。唐以前,从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中说的“今此州户万有余”,可见已有一定人口,也已有一定的经济规模。但毕竟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蛮荒之域。且潮州原为蛮獠聚居之地,《隋书》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拖,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潮州也常因蛮獠啸乱而生战乱,因而长期处于缓慢的开发之中。直到唐代之后,陈元光平定蛮獠啸乱,创建漳州,而后则有常衮、韩愈等兴学重教,开发潮州,潮州的经济文化才得到明显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对于唐代的潮州来说,首先是人口的增加。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中原人民纷纷南迁,潮州成为移民浪潮之重要承接地,人口有较快的增长。据黄挺、杜经国《潮汕地区人口的发展》(唐——元)一文统计:“潮汕地区开元间(741)大约有37000人,贞元十七年(801)大约有40800人,从贞元十七年到宋开宝初(969)近170年,本地区人口数量增加268%,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6.8,按此增长率计算,到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本地区人口总数接近80000人,这是唐代潮汕地区的人口峰值。”中原之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生产生活模式,兴修水利, 改良农田,促使潮州地区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除了水稻、蚕织等传统农耕生产之发展外,具有本地特色的煮海盐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35之“海阳县”条便有如下记载:“盐亭驿,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记载虽未详,然“远近取给”一词,则可窥见一定规模之海盐贸易迹象。此外,唐代潮州的陶瓷业也已有一定的规模。上世纪考古工作者从潮州北关、洪厝埔、竹园墩等遗址挖掘了一批唐代陶瓷遗存,典型者如“潮州北关窑址的青釉加彩平底碗、青釉二系短流盖壶、揭阳出土的双耳注、青瓷四耳樽、瓷钵,澄海的大水瓮、小水瓮”等。一叶而知秋,由上当不难窥见唐代潮州陶瓷业发展之颇为繁盛状况。
一定的经济发展是文学萌生、滋长的基础,而一定的文化氛围则是文学萌生、滋长之温床。然而,潮州古代文学之滋生,自身文化进程之孵化远非外来文学之移植来得快捷,而历代莅潮官员之文学移植与栽培便是其萌生、滋长之首要外在因素。因而萌发伊始之滥觞期,潮州古代文学主要是由寓潮作家在潮期间的创作和本土作家之创作两部分构成的。这是潮州古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潮州古代文学萌发伊始,便呈现出较高艺术水准之重要原因。
唐代以前潮州文学萌生、滋长之程度如何,均无史料可考。而有史记载之文学史料,直至唐代以后方始出现。因而,我们只能这样说,唐代是潮州古代文学之滥觞期。
有唐一代,有史料可考之作家作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寓潮作家在潮创作作品:韩愈的《别赵子》等诗和《祭太湖神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祭止雨文》等文。李德裕《到恶溪夜泊芦岛》等诗和在潮杂序集《穷愁志》等。二、本土作家作品:陈元光之《漳州新城秋宴》《晓发佛潭桥》《示子珦》及其后人辑录的《龙湖集》;赵德之文《昌黎文录序》,以及释大颠之《退之别传》。
寓潮作家多为国内文学大家,其寓潮作品,只是该作家一生文学生涯之一个小小浪花,其作品对潮州古代文学之发生、发展虽然影响很大,然作为外来文学因素,其影响毕竟是比较零碎的,不连贯的,局部的,因而,不是影响特别大的,我们只做一般的介绍。而着重介绍、分析、论述的是本土的作家作品,他们才是潮州古代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之主力军。遗憾的是,有唐一代,存世的只有陈元光、赵德、释大颠等极少的零星资料。
陈元光著有《王钤记》,已佚。其遗存诗篇共50首,《龙湖集》48首,《漳州府志》《漳浦县志》《云霄县志》的艺文志中载有2首。其中有3首入载《全唐诗》,有4首入载《全唐诗外编》。陈元光的诗大多因时而赋,因事而作,因景而咏,具有史诗的叙事底蕴,是他一生开发泉潮南方边塞大业的缩影。陈元光的诗展现了诗人平蛮开漳之浴血奋战历程,生动地描绘出初唐泉潮南方边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风情画面。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唐初南方边陲特有的妍丽风光、风土民情以及开发南疆的艰苦创业画面。既是他一生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唐初泉潮南方边陲经济文化开发初始的壮丽史诗。
陈元光13岁随父出征泉、潮南方边塞,平蛮屯垦,开发南疆,直至为国捐躯,历时42年,尽管其潮籍身份存疑,但其潮人作家之身份则是无可置疑的。就目前文献所及,作为唐代凤毛麟角的潮人作家,其诗歌创作,即使仅有直接写于潮州或以潮州为题材的《修文语士民》《祀湖(潮)州三山神题壁》(三首)、《平潮寇》几首诗,无疑也都是潮州古代诗歌乃至潮州古代文学之开山之作。陈元光的诗重兴寄,有真情,开创了潮州古代诗歌刚健峻丽、清新明快诗风。其审美内核与后世岭南诗风一脉相承,应是岭南诗派之开创者之一。
赵德,号天水先生。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摄海阳尉为衙推官专领校事。韩愈离潮时,赋诗以别,并以生平所作文授之。赵德遂将所赠文章72篇,编为《昌黎文录》6卷,并为之序。这篇序文,便是至今遗存的唯一一篇天水先生的文章,也是至今能够见到的潮州古代文学最早的一篇散文作品。
赵德之《昌黎文录序》一文,核心意涵在于阐述韩愈是纯正的孔孟之道的“圣人之徒”,其文章“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践行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昌黎文录序》)。韩愈倡导之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健康的发展道路。其实质就在于复兴儒学。《昌黎文录序》旨在赞颂韩愈孔孟之道之纯正,奠定潮州孔孟之道之儒家正统地位,成为潮州古代文学儒家正统血脉的基石。
释大颠著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义》《金刚经释义》《大颠偈》等。今存《退之别传》一文。释大颠住持灵山禅院时,有韩愈问道留衣千古佳话,《退之别传》即为韩愈与大颠问答之记录。该文描述了韩愈祀神海上,访释者大颠,与大颠的一场社会、人生、宗教、哲学之高峰对答。
大颠与韩愈之对答,展现了释者与儒者哲学核心之本质差异。释者为方外之人,其追求在于道之高远,着眼于普度众生,其观照的世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儒者着眼于入世,追求仁义忠信,立足于建功立业,为君所用,尽忠尽孝,“屑屑于形器之内,而奔走于声色利禄之间”(《退之别传》),其观照的世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韩愈之“道”,虽然与孔子之“道”有理解上之偏差,然都是入世之道。一出世,一入世,判然有别,非是非曲直之辩也。
《退之别传》如实描述了韩愈与大颠的儒释对答论辩,展现了一代文豪与一代高僧之泱泱儒释风范。韩愈与大颠的对答,是儒释在唐代潮州地域上的一次具有哲学高度和深度的对话,影响甚为深广。韩愈之问道大颠与孔子之问道老子,异曲而同工,垂范后人的是治学之严谨与不耻下问之谦谦君子形象。大颠学识渊博,玄远高深,垂范后人的是高屋建瓴与机锋妙悟之世外高人风姿。
唐代是潮州古代文学之滥觞,荡漾在潮人文学历史源头中的虽然只是几朵微弱的浪花,然而,这几朵微弱的浪花却既蕴涵着刚健入世、清新峻丽的诗风,也蕴涵着玄远幽深、机锋妙趣之文韵。可见,潮州古代文学滋长伊始便呈现着潮州古代以儒佛交辉为底蕴之多元文化因子,并使之成为潮州古代文学以积极入世、刚健峻丽、清新明快为主,以空灵妙悟、恬淡闲适、幽深渺远为辅审美风韵之基石。(续完)
翁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