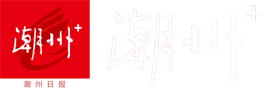粥,潮州人叫“糜”,两者的关系,如同空气和水,按我们的话说:“一世人离唔开糜。”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食糜这个习惯,始终不变。糜有各种各样,我食过的糜,不下十来二十种,有的糜,还带着故事,带着时代的味道。
北方人称粥为稀饭,他们的稀饭,是名副其实的稀,稀到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被人奚落为“照影稀饭”。一听潮州人天天喝稀饭,不免摇头,认为很穷。我常解释:“不是这样的稀饭,我们的糜很稠、很粘、很香……”我还只是说了最普通的一种:白糜。
小的时候,我吃过的两种糜,印象深刻。那时候长身子,回家看有食剩的糜,就感到肚子饿。开始加热食,慢慢便食出了花样,仿照鲜美的水鸡糜,我到菜园钓来几只青蛙,炖了一碗青蛙糜。母亲每次煎了咸鱼之后,总会倒下一碗糜“洗鼎”,这种“咸鱼糜”,味道独特,我很爱食。
参军时,正遇到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饥饿时期”。我们连队大多是潮州兵,日子有些难熬。部队以面食为主,本来就很不习惯,后来粮食定量,供给的面粉做馒头、包子不够吃,无奈,只好在面里掺进切碎的芭蕉头,越掺越多,难以下咽。大米断供,粥也喝不到了。事务长是潮州人,设法拿面粉换了点大米,遇到连队训练劳动强度大、天气热,便以补水防暑为由安排炊事班做点绿豆粥,让老乡们既解暑也解馋。
难忘第一次在北京食糜的情景。1968年初冬,我到北京参加海军新闻干部学习班,住在停课的煤炭学校,吃早饭的时候,端上来金灿灿的窝窝头,以为很好吃。那时有定量,每人两个窝头一碗粥,兴冲冲咬了一口窝窝头,大失所望,没有味道,干硬干硬难以下咽,勉强吃了几口,跟吃药一样。粥也不好吃,稀得很,但毕竟吃得惯。正发愁,忽然想到同人家交换,两个窝窝头换一碗稀饭。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这种交易谁不乐意。于是两个月的学习时间,我的早餐天天只喝两碗“照影稀饭”。开会、学习又不能吃零食,肚子常饿得咕咕叫。关心我的人教我喝点啤酒补充营养,说啤酒是液体面包,那段时间,我的军用水壶,装的都是啤酒。
学习班结束,我调入海军报社,开始了大半辈子的北京生活,也经历了与糜的若即若离、“悲欢离合”……
很长一段时候,我吃不到好糜。“困难”的那个期间,什么都凭票供应。每个月限量的几斤大米,买到的都是仓库的多年陈米。淘米时要捡“丝虫”,做出来的糜米是米汤是汤,一股霉味,很难喝。只好按照北方人的习惯,吃油条,啃馒头。探家时,母亲拿旧米到乡下换新米,我才吃到真正的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好日子的到来,又见家乡的糜了。好米随便买,想吃就做,还吃出花样来,鱼糜、蚝(蛤蜊)糜、牛肉糜、虾糜、蟹糜,还从道钿弟那里学会做鱿鱼糜。就像野菜成了宴席宠儿一样,鱼肉吃腻了便改做菜糜,样式就多了,番薯糜、南瓜糜、芋头糜、白菜糜、春菜糜、飞龙(菠菜)糜,还有“八宝糜”。那回儿大姐和李兄来北京,住在儿子家已有一段时间,估计会“想食”,我特意做了一顿“鱼糜”招待。买了活草鱼,煞有介事,片鱼、去皮、切片,放进滚烫的高汤、热饭,撒上青葱、香菜、胡椒粉,做出了像模像样的鱼糜。大姐尝了一口,点了点头,让我再加点鱼露,说才“杀嘴”〔爽口〕。一次探家,有写作任务,每晚熬夜。一天夜半时分,弟弟同往常一样,轻轻地在我的案头放下夜宵,轻轻地走开。我放下笔,美美地吃了一碗很甜很甜、甜到心里的糯米糜。
退休以后,时间宽裕了,我开始像家乡人一样,每天早餐食糜。在京潮人几天没吃“白糜”必想,潮菜宴席,潮人家宴,菜肴再丰盛,总还得白糜侍候。白糜看似简单,做好不容易。潮汕人嘴刁,一嘴糜的质量能分出毫厘。北京“仰山楼”老板阿章,宴请潮州来客,选饭店舍近求远,只因为“这家饭店的‘白糜’好食。”我探家时留意弟弟和妹夫煮糜,学会了米与水、大火与小火的掌握,早上煮糜,既轻松又好食,北方人的老伴也学会了。更称心的是,以前咸菜要从潮州带,现在北京就能买到,菜脯、咸菜、贡菜、橄榄菜、腐乳、丁香鱼,“鱼饭”,自制咸带鱼,应有尽有,有时潮人联谊会活动,商家还会送货上门。
食白糜,配咸菜,听潮乐……“家”在北京。
糜,是家乡味道。
糜,是潮人骨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