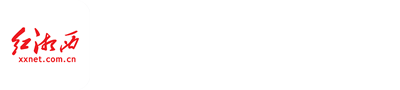重振旗鼓
一般而言,一首歌曲能有一个亮点已算不错,但《子》至少有两个。其一是歌词的文字游戏让人愉悦,其二是摇滚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嫁接让人思考。而对湘西人来说,亮点可能更多。
作为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盛行于酉水保靖县河段的船工号子可谓是古老沧桑的说唱,虽然号子随着酉水船运一同衰落,但其中蕴藏的与大自然较劲并和解的精神力量,是永恒不灭的,绝非装腔作势的梦呓口技可比。哪里有河流,哪里就有这种力量,很多人音乐人应该都有留意。

崔健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中收录了一首《城市船夫》,原名《江水号子》,这首歌的名气虽远不如崔健的那几首“流行歌”,却展现出崔健作为音乐家的思想高度,他将黄河船夫的号子与现代城市的声音采样编织在一起,让人沉浸在心荡神迷但利欲清醒的奇特世界。在2015年,我就跟罗卿提起,把酉水船工号子放进摇滚乐里充当Rap,应该会出彩,不过当时素乐团第一张专辑已经接近完工,这个创意就搁置下来。2015年底,谭维维与陕西华阴老腔艺人推出惊艳一时的摇滚歌曲《给你一点颜色》,这一文化事件更加坚定了我促成“号子摇滚”的决心。

2016年初,我便开始打听民间喊号子的艺人。毕竟是第一次尝试,为了尽量降低罗卿与之磨合的难度,我定下人选标准,不考虑年事已高的老艺人,而选择舞台经验丰富的青年歌手,最终我将目光锁定在保靖人张明松身上。张明松对酉水船工号子有一定的收集整理,他的说唱未必有十分的原真性,但表演性强,急促带劲,有感染力,很适合号子的再创作。6月3日,我邀请张明松与吴廷翠(苗族女歌手翠翠)来不隐斋做客,共商合作。二位既是非遗传承人,也是歌手,我们沟通很顺畅,初步敲定的是:张明松的一大段号子说唱将与罗卿的现代摇滚进行平等对话,不光是碰撞,还要融为一体,而为了化解两种声线两种风格的强烈反差,可用翠翠苗族民歌的天籁之声作为结尾。这一切的设计都是在没有主题没有歌词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未通知罗卿方面。
随后几日,我在书房搜肠刮肚,推翻了多个题材。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缩小罗卿和张明松的差异性,罗卿的音乐是一贯的文火煎药,但药到病除,张明松的号子则如狂风扫叶,气势汹汹,却是打在身上还很舒服的机关枪,如果嫁接以后的歌曲还是明明朗朗分为两块,作品就散架失败了。而严峻的是,号子唱词本就有相应的格式与节奏,那么歌词创作一定会分两个板块。如果让罗卿和张明松用不同的风格来唱同一套词,那就成了内战。我想到的办法是,用一个开放性与包容性极强的主题将两套演唱体系贯穿起来,首选是汉语里的万能名词后缀“子”。有了一条明线,便可量身定做唱词了,罗卿的部分写得神秘典雅一些,用先秦诸子压阵,张明松的部分写得直白俚俗一些,用房子、车子、命根子等等串联,两个部分看似缤纷,实则一同指向人性,不要忘了,这还必须是一首有内涵的摇滚歌曲。当然,我也担心这个创意玩得太高入云端,脱离了群众,于是又加入了一个小设计,就是把号子唱词格式中的“哎”“嗨”等衬词换成了实词,即湘西人的两大口头禅——“扎实”“恼火”。后来证明,这个艺术加工精准地戳中了乡亲们的兴奋点。
大概用了两个小时,《子》的歌词初稿完成了。我又推敲了一个下午,这才发给罗卿。为了强调这首歌的分量,我特意在邮件上注明“神曲”二字。这一次,罗卿接招了。

几日后,我、罗卿、张明松、翠翠四人在罗卿工作室会面,大家一致通过了词作的设计。接下来的编曲和录音环节,果不其然,罗卿主要在处理与张明松的融合问题。就这样,耗时一月,素乐团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子》问世了,我和罗卿决定先放在社交网络上提前预热。
《子》这首歌曲之所以能成为素乐团的代表作,长期位居乐队歌曲收听榜的头名,是因为它具备了后来我们所提出的“文化摇滚”主张的所有特征,它将我一个著书人的擅长、罗卿一贯的音乐趣味、湘西人的性格以及摇滚乐的精神都呈现出来,这些方面任去其一,歌曲都将失色,因此,《子》是不可复制的。
或许也是通过《子》,罗卿确信了我俩作为词曲搭档所产生的威力。
一个秋夜,乾州古城里的茶肆生意兴隆,而罗卿约我在僻静的“有味书吧”见面。他要和我谈一件很重要的事,重要程度堪比初见。现场不能没有人,怕谈崩了尴尬,也不能有太多人,怕嘴杂干扰。
他说,我想你正式加入乐队,歌词由你专职,以后乐队的所有收入都有你一份。我说,我和你玩音乐从来不是为了钱,我愿意加入,也自信能够胜任。一分钟,谈妥了。
不到两年时间,我和罗卿从君子之交,到合作蜜月,到隔阂冷战,再到终身队友,可以说,在私人感情上,我们是知根知底,心照不宣了;在合作关系中,我们是互相鞭策,互相提升。我不止一次跟旁人讲过,我会和罗卿玩下去,享受创作的过程。对,创作,这是最让我不能自拔的因素,身外物,我不在乎。我没说出口的是,如果有一天,罗卿不认可甚至不承认我的创作贡献,我在乐队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了,那便是我离开的时候。读书人的个性,立此存照,天人共鉴。呵呵。
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罗卿跟我谈起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刚发现的年轻乐手陈勤,这个90后小伙子外表文静,还保留些学生气,但他在大学期间就玩了四年乐队,有一定演出经验,毕业后又在吉首做驻场乐手,颇有音乐天分,罗卿想将他培养成乐队的新任贝斯手。

另一个人,罗卿说非常重要,必须带我拜访,去深圳。
2016年10月13日,早有提名的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突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似乎真正被接纳进荷马和萨福的谱系之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呜呼!除了从唐诗走向宋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我又多了一个应证这份事业的外国的现代材料。不过鲍勃迪伦对获奖一事进行了冷处理,有礼有节也不卑不亢,这本身很摇滚,资深的摇滚。第二天刚好是罗卿的生日,诺奖的消息传遍中国,大家都在谈论这一次的“出格”。我问罗卿的看法,他回了一句:知道,他很厉害。又补了一句,年底去深圳,安排好时间。
2016年12月,我和罗卿从怀化乘高铁来到深圳。深圳这座城市很特别,得习仲勋、邓小平等大人物的垂爱,拥有与生俱来的话题体质,他年青得看不见任何历史包袱与文化沉疴,倒有一身的激情甚至冲动。有人说他是一片荒漠,两万基建工程兵曾在这里拼命拓荒;有人说他是一方乐土,没有外来人概念的移民城市;有人说他是一种精神,“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就差刻在人们的脑门上;有人说他是一种速度,从小渔村至今,经济总量的增长超过2万倍;有人说他是一个梦,可以诞生腾讯和华为这样的奇迹,且不需要做那些奇迹的前缀;有人说他是一种价值,宽容失败,鼓励创新。……
我觉得,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审视,深圳堪称整个中国史上的“特区”,深圳是一批批背井离乡的人聚在一起,围成白纸作画、平地起楼的试验田,是一批批治理者同国家大政方针互动,修炼智慧与胆魄的示范区,也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的青春橱窗,是中国文明再次远航世界的不夜港口。而对于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深圳都会保护他们的乡愁,无论你来自何处,到了深圳,你就会变成深圳人。深圳人和深圳一样,都在不断试验,试验某种路径,某种想法。

让我确信这一点的,正是罗卿音乐事业的引路人阿飞。
阿飞,文艺气质浓郁的名号,主要流行于音乐圈,乡亲们则尊称一声飞哥,有几分江湖味道。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本名涂飞,他身材魁伟,站可遮风挡雨,坐如铁壁铜墙,长年坚持穿戴简约文化衫与深色帽子,给人一种低调却深不可测的印象,好在黑色镜架帮我迅速锁定那对圆睁的眸子,倒很诚恳,向下则是两瓣丰厚的嘴唇,似要吐出金句来,不料,多是些湘西俚语。他走起路来,十步之内,必要耸耸肩背,一派憨态,一席轻松。
飞哥说他生于成都,长在吉首,自称湘西土锤,少年时钟情于绘画、阅读、书法,后来去长沙卖打口碟、玩音乐。他在一支名叫“橡皮人”的乐队里担任主唱兼主音吉他,后来同乐队“飞”到了深圳。
十年时间,阿飞成长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意代表之一。在一份“中国商业最具创意人物100”的榜单中,涂飞的名字赫然在列。他的身份多元,但每份事业都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并乐在其中。一会儿是国内独立书店代表“旧天堂”的老板,他从深圳电子步行街华强北的小地摊起步,做成了华侨城创意园里200多平米的实体书店,不仅靠卖书盈了利,还打造成举办知识分子沙龙讲座和独立音乐演出的文化空间;一会儿是国内最成功的Livehouse——B10现场的合伙人,B10现场一年承接世界各地艺人的200多场演出,涵盖实验、先锋、摇滚、爵士、民族等音乐类型,俨然是一个国际性的艺术中心;一会儿是深圳OCT-LOFT国际爵士音乐节与明天音乐节的策划人,制造华侨城创意园一年一度的盛大狂欢;一会儿是深圳电台音乐节目“行走的耳朵”的特邀主持人,每天花几个小时选择音乐来做解读和推广;一会儿是巴塞罗那的死忠球迷,和队友们踢球撸串。
如果说华侨城创意园是深圳的地标,涂飞就是地标的地标。这个至今无房无车无小孩只烟不酒的男人,耗资巨大经年累月地收藏着世界各地的黑胶唱片,租屋里的书籍、磁带、碟片以及音响设备,堆积如山。
阿飞,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自强却自在的立身方式,不止于此,我们还领略到相互认同的人自然聚集,更领略到文艺对人的塑造,以及文艺受益者对文艺的回馈。他所交往的高人,他所处理的事务,他所制造的影响,其密,其巨,其久远,足以让一大批文化官员相形见绌。为此,我和罗卿专门创作了一首讽刺歌曲《文氓》,表达对涂飞先生的崇敬。他这样的人,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被视为土匪,却干着圣人的事,而一些官员反之。
直到面见飞哥,我才真正理解,罗卿不愿掺和本土圈子的原因,深圳已是他另一个精神家园。罗卿与阿飞交好多年,亦师亦友,两人坦诚相待,直言不讳。阿飞的指点,罗卿多半是虚心接受,这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此次深圳之行让我回味,盖因收获有三,一是结识了阿飞这样一位堪为身范的大哥,二是敲定了素乐团2017年新专辑在B10现场的首发演出,三是素乐团的摇滚主张初步成形。
在我们辞行之际,飞哥半开玩笑式地交待了一件事,这件事他后来又敦促了几回,我才知道是认真的。他给我和罗卿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主题就是“峒河布鲁斯”,用方言演唱。
表面上,这只是一首满足飞哥个人思乡情结的歌曲,其实不然,他还提供了一个创作思路,打造一首融通母亲河、家乡话、现代流行音乐根源这三大要素的作品,执行起来就是在布鲁斯音乐的基底之上用吉首话歌唱峒河。我想,当年昆曲鼎盛之时,“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那么这首歌也应该要具备推广家乡话的功能,歌词和演唱要尽量把标准的吉首方言呈现出来。
虽然素乐团的《峒河峒河》在2017年底才推出,但他在本土所引发的热议,证明了飞哥的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