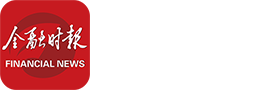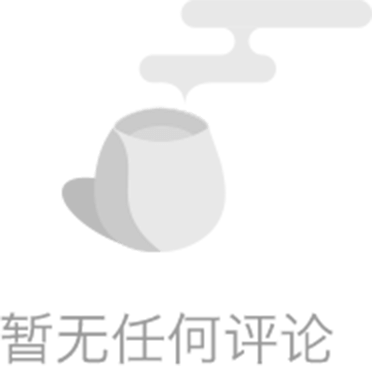策划人语 近来,电视剧《三十而已》热播,剧中关涉的“精致穷”“顾学”“净身出海”等热词引发了现象级热潮。该剧取材于日常生活,从三位女性的视角,呈现女性的职业观、爱情观、家庭观。该剧得到多个年龄层观众的关注,有二十几岁的青年、有年已花甲的退休族,而发表议论颇多的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综观现当代文学史和影视剧,“女性群像”的刻画以及有关“女性独立”意识的探讨,颇有可圈可点的佳作,而女性的地位、女性的思考、女性的生存状态,恰恰也是整个社会的“晴雨表”。

日前,都市情感剧《三十而已》引发争议。捧之者曰“完美”,曰“独立”,曰“正能量”,曰“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棒”之者曰“口号”,曰“概念”,曰漏洞百出,曰“傻白甜”。当然,争议不是坏事,说明思考正在逐步深入。文学批评家圣勃夫曾说,引发思考最多的就是佳作。
关于《三十而已》的“而已”
“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其实,《三十而已》这部剧,二十几岁的青年也在看,年已花甲的退休族也在看,而议论最多的,反倒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为什么?因为触动了自己的某一根神经。无论是创业、沪漂、销售、写稿、复婚、出轨……大家都在剧中“寻找自己”。因此,仅仅圈定该剧“女性剧”的半径是不够的。“永恒之女性,带领我们走”——女性的“情”与“才”,每每能够迅速拉动社会情感的节奏,而女性的地位、女性的思考、女性的生存状态,恰恰也是整个社会的“晴雨表”。

王漫妮进进出出“魔都”,充满人生际遇的隐喻,“艰难困苦,玉汝以成”,自己成就自己并非易事。钟晓芹从本土小女孩一夜长大,几乎不可能地突然成为作家,其经历告诉“温室女”:恋爱和结婚绝非一回事,独处是成人的阶梯。“完人”顾佳把生命规划为表格,一切做得仁至义尽;无奈的是,现实中哪里去找寻智商情商“都在同一线”的另一半与幸福感?总之,本土女孩都想成为钟晓芹,外来的“王漫妮们”都渴望成为下一个顾佳,这是男男女女都正在面对或必将面对的社会话题。也无怪乎观剧的比例,男性并不少于女性。
有评论说:“我们不妨多多关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三十岁女性。无论是她们的职场困惑还是家庭烦恼,都还有太多值得言说的地方。”把“三十岁”改为“四十岁”“五十岁”同样成立,把“女性”改为“男性”亦无不可。所以,“三十”仅仅是一个“社会生活年轮”的符号,编剧的立场或许在于“而已”。
《三十而已》的剧名,官方给出的翻译是“Nothing But Thirty”,其随情任性、洒脱英飒跃然纸上。“Nothing but”在英语里是常见词组,意为“只是,仅仅,只不过,无非,除……外”。无奈现实生活不是演戏,“而已”作为一种超脱式抒情可以,作为“向前看”的励志也可以,但是,看看自己的四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同事,看看剧中三十上下的百步九折的男男女女,能够“哪管他去早了黄鹤来迟了青莲”的潇洒者,凤毛麟角也。
鲁迅说:“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环境改造人也“压迫”人,“三十”是沉实的开始,而不是盲目潇洒。

关于“女性群像”的历史
对于《三十而已》,评论说“时下大上海女性群像的首次成功绘写”,或许尚可;但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群像”是“早已有之”,不可贸然冠之“第一”。
比如,70年前的“解放区文学”作品、阮章竞的《漳河水》,成功塑造了荷荷、苓苓、紫金英三位农村妇女形象。她们的婚姻不幸正是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写真。而三者经历、性格各有不同,但终于在“反倒了封建”的大纛之下扬眉吐气,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次呼出“现代气息”的女性群像,尽管现如今那个群体的困惑已经翻篇。
1981年,足以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小说《方舟》问世,作者张洁两获茅盾文学奖,是典型的“女性文学”作家。而《方舟》里的三个知识女性——学者、翻译、导演——都是经历了历史磨砺而离异或者分居者,在同一套公寓房的“方舟”里,她们为事业、为孩子马不停蹄,与居无定所的孤独感、漂泊感搏斗。小说的题记——“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是焦灼的、悲凉的,但字里行间的思考却凝聚了老一辈知识女性的悲欢离合,是如今“三十而已”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
在电视剧中,诸多“女性群像”也可圈可点。比如,1991年,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在央视播出,轰动全国。六个从穷山沟赵家坳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命运,展开了我国内地、沿海、香港三个地域文化层面的故事。陈小艺扮演的女主人公赵小云及其姐妹们的形象不胫而走,在磨难中成熟的打工妹的群像家喻户晓。迄今为止,其“群像”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延续至今,《三十而已》主旨之一的话题仍然是:走出了乡野,走向了现代,下一步还往哪走?还能够回得去吗?
再如,2005年,影视屏幕上一帮才子才女“恋爱横溢”,诸多电视频道热播《好想好想谈恋爱》。有的省如安徽从早上5点多开始播到下午,“培养”了大批爱情实践的探索者和各个年龄段的爱情理论专家。有点巧合的是,该剧的人物群像也是30-33岁的白领女性,同样是20-23岁或40-43岁的人兴致盎然。因为谭爱琳、黎明朗、毛娜和陶春代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女性,其优雅不俗、爽朗直白、风情万种、乖巧任性早已超出了年龄的界限而成为个性符号。而该剧是以对“情爱哲学”的思考为经纬的,其情节的淡化、不连贯,人物关系的松散、随意,人物性格逻辑漏洞,拉开了与大众的距离。

关于“独立意识”的嬗变
“女性独立”的问题,从18世纪玛莉《女权辩护》的启蒙,到20世纪波伏娃“帮助一代男女获得更多的智慧与自尊”的《第二性》,论述已经汗牛充栋,认识也日渐深刻。然而,从《方舟》到《三十而已》,窃以为严格意义上的“女性独立意识”并没有多大进步。
《方舟》里的女性群体,在岗位上成就不凡,也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压抑作为女性的诸多需求,而伴随对男性的失望、怀疑,为了新的人生目标,在压抑中坚忍前行,不无悲剧的崇高感。
《外来妹》的主人公,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毅然“下嫁”一位电工的卡捷琳娜,女性的独立意识同样鲜明。而《好想好想谈恋爱》里,“女性群像”的言行颇多不一致,她们一边说“风情万种是上天赋予女人的天赋,因为是男人爱你的先决条件”,似还是以男性为中心,但其举动又充满了对男性的揶揄、讥讽、不信任,独立意识又跃然纸上。
相比之下,《三十而已》曰“做做全职太太也无妨”,以及如何“套路”自己喜欢的男人,反倒是有了几分“独立外表下的不独立”乃至“附庸”的味道。
总之,女性的独立,不仅仅是为老公做“人设”、设计包装;不仅仅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千斤重担一身挑”;不仅仅是痛斥乃至痛揍“小三”;而是“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在这个意义上,《方舟》与《外来妹》或许更值得回味。而《三十而已》之所以上热搜、引发议论,与如今的需要自我鼓劲儿,与众多“精致穷”人群的共鸣息息相关。
那个写了《龙的传人》歌曲的作者,还有另一首重要的歌:《三十以后才明白》:“三十以后才明白/要来的早晚会来/三十以后才明白/想爱的尽管去爱/……大江东去浪淘尽/一代又一代/更有新一代/谁也赢不了/时间的比赛/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
是的,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不会走远,女性的进步无可阻挡,何况从象征意义上考察,我们都是——三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