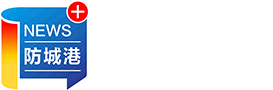● 任万杰
我家房子前面,一个楼盘工程开始建设了,一条供工程进出物料的大路也一并修成通车。几乎每天我都要从这条大路通过,因为它是通往市区最近的路。黎明的时分,墙外路面传上来像蚕吃桑叶一样的沙沙声,很缓慢,很有频率和节奏,并且很有力地持续着。
踏上这条大路就会发现:一位老者手里横着一把很长自制的专用扫帚,一下一下缓慢地清扫地上的浮尘和拉土车颠下来的建筑垃圾。他的手用力压得很低,地上的浮尘就飘不起很高,扫帚划开3米左右的半圆,就像蚕在吃桑叶的边缘一样,随着沙沙的声音有节奏的响起,身后出现一条干干净净地大路。
我发现他的眼睛几乎只注视路面,戴着一顶边沿有些微微破损的草帽,能看见耳朵上夹着的一根自己卷制的抽了一半的旱烟,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鼓着口袋的中山装,下身泛着白的黑裤子遍布灰尘和泥点,左裤管挽的很高,清楚地看见左脚蹬着的几乎辨不出颜色的拖鞋,身后蹲着一条四蹄白毛全身漆黑的狗,耷拉着耳朵,老者向前缓慢地前进,距离稍稍一远,那条狗就站起来,不离不弃的往前跑几步,又蹲卧下来耷拉着耳朵。
老者的手一直没有停止挥舞,虔诚而又坚定,眼手一处,心无旁骛,干净的路面随着他穿着拖鞋的脚在缓慢的延伸前进着。四车道宽的路,我从来也不知他要扫几个来回。每天早上路过时,总能看见老者和狗。晚上归来路过,却总看不见老者,偶尔看见那条黑犬和几条流浪狗一起在树林里疯跑。
几乎没过多久,当路东边树林里的花椒树长满一树的花椒叶子,花椒的鲜香气味就引得好些人来,摘几把新鲜的椒叶去做下火的清汤面吃。路西边的楼盘就好像竹笋发节一样地向上冒,水泥罐车就不断地出出入入,这条四车道的路,有时竟然停留一摆子等待下货的车。
院子里的石榴树开花了,一树的红。清晨从树下经过,能闻到幽幽的香。唯有早上听不见车的嘈杂和建设的噪音,听得见的只是南墙外老者扫地的沙沙声。
老者依旧很缓慢有力地挥舞着自制的竹扫帚,戴的草帽子有些黄旧,依旧穿着那双旧拖鞋,那条黑犬依旧卧在老者身后不远,偶尔竖一竖黑耳朵。干净的路在老者坚定的脚印下一步一步在伸展。偶尔一阵风吹的杨树叶子手掌般翻转,那条黑犬就立即站起来,像豹子一样吠叫着,去追一只在林子里露头的猫。
天气热的时候,路上的浮尘也飞扬得很高。朝霞照在大路上,那位老者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服装,那条黑犬只不过略显得有些瘦长,但依然伴随在老者的左右,寂寞中带有威严。我从来没有听见老者说一句话,只是见到他坚定而又自信的压低手中的扫帚,扫干净脚下的路,把浮尘压到最低,在身后显现一条洁净的大道。
当知了断断续续的鸣叫在树梢头时,第一片叶子在知了有一声没一声中开始落下来。街边的银杏树就全部变成一树的黄金色,开始有人拿个布袋,在树下捡拾黄金一样的叶子去装枕头,甚或用脚蹬一蹬银杏树身,摇落一地的黄色。地上的落叶开始有风卷起,墙外的大道上,那把几乎用了一年的自制扫帚,依然在坚定地挥洒,没有多少的磨损和脱落,大道上的落叶让老者多了几分自如,他的拖鞋不知何时换上了一双裂着细细口子的运动鞋,一只鞋带是黑的,一只鞋带是白的,一黑一白在交替着前进,一片干净的土地就在这交替中拓展开来。
后来,随着工程的结束,我再也看不到那位老者和他的黑犬,或许是跟着施工的队伍一起开拔迈向下一个工程,也许那个工地上还会有一条大道需要每一天把它扫干净。我想,人的一生,很像是这条路,我们在人生路上前行,要像这位扫路的老者,每走动一步,都要干干净净,不但为自己,更多的是为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