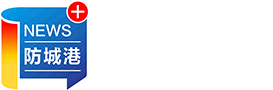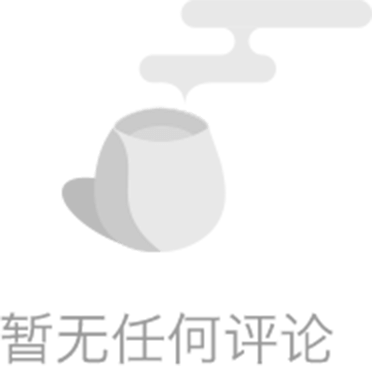● 刘 放
看电视新闻,每每看到国歌声中升起五星红旗的镜头,我总会眼前闪现当年村小升国旗的情景。
村小,当时叫大队小学。我们是六大队,校名自然就是“六大队小学”。
村小的格局是一个口字形,两排相对教室的两端,一端是顺坡而建的土台,一端做一个留门的围墙,四面包围的中间是操场。操场是本色的泥地。与土台、教室、老师办公室的地一样,都是泥地,不铺砖,不浇筑混凝土,更不可能铺设地板,十分接地气。教室没有天花板,抬头,能清晰看到那一片片瓦,如同我们的肋骨,为我们阻隔屋外的天。墙上的窗户用塑料薄膜钉起来,这样刮起大风、下斜泼大雨,我们风雨不惧,还能免费听大自然的天籁。
校园四周是大片的农田,记忆中,除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美好之外,也有不好处,就是农田浇起粪来校园处处臭气弥漫。有时在上课的课堂上,有女生彼此面面相觑地窃笑,还下意识用手掌鼻端挥一挥。老师不高兴了,说,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说得该女生低下头,很惭愧的样子。
全校五个年级一同操场上活动,那是早操。早操是体育老师在土台上领操,嘴上喊口令。在做操之前,要举行升旗仪式,土台上有旗杆,顶端有一个滑轮,绳子将国旗一截一截升到顶。这个过程,整个校园一片肃静。升旗完毕,随着老师的口令,大家一起望着国旗行少先队队礼。
少年的记忆中,我曾在这个环节,大出过一回风头。那就是,我用竹笛吹奏国歌,竹笛声中国旗冉冉升上村小土台的上空。
我吹竹笛完全是无师自通。那阵子,村里住有地质队,工人在附近的田间搭井架钻探,租住在村里。在他们休息的时间里,我看到一个会吹笛子的青年教另外一个同伴吹,旁观到了指法,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第三孔作1、闭孔作5的音阶排列。我非常向往笛子,就靠自己锤石头挣得到的一点钱,花两毛六分,买了一只竹笛,贴竹膜,自己琢磨着吹。奶奶见了非常高兴,她眼睛里放着异彩,对我说,下午吹的就明显比上午好听。晚饭后再吹,她又说,晚上明显比下午好,都成调了,明显是一支歌了。我与奶奶相依为命,不但早晚在小屋中吹她不嫌烦,就是半夜醒来,我还要拿起枕边的笛子吹一段,她也听得津津有味,眉开眼笑。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六大队小学有一名小小竹笛手。
那天,当开始升旗的时候,我提前躲到土台一边的一片小树林里,仰望冉冉升起的国旗,精神抖擞地吹奏了一曲完整的国歌。那是在早晨的旭日下,我似乎感觉到红旗明显比往日更红,而我兴奋的脸蛋,大约也是红如小公鸡的鸡冠。周围的稻田秧苗怎么样?在教室屋脊上麻雀的俯瞰中,也许会随着红旗的飘舞和我竹笛的旋律而荡漾起欢快的碧波吧?这是本村小,有史以来第一次师生视觉和听觉一同感受到“国”的存在,感受到自己的脉搏、呼吸,可以与一支旋律和一面旗帜融为一体……我吹奏结束,听到了操场上兴奋的掌声一片!
一晃此事件距今快半个世纪了,村小也早已旧貌变新颜。我不知那片小树林的树长成多大了,如果任其自然生长,那些树唱片一般的年轮中,似乎就该烙印上了一段意义特别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