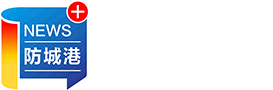● 蓝 天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南屏瑶族乡工作。
又一年的秋天来了,田野一片金黄,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乡村的土地上,乡亲们春夏飘落的辛勤汗水,终于获得了沉甸甸的回报。
下午下班后吃完饭,太阳依然在西边的山头,红着脸儿洒下柔和的光芒。
从饭堂漫步到乡政府大门口,见到东边百把米外的稻田里,有乡亲正在割稻谷,我很有兴趣便走过去。这是一片几十亩的良田,临着南屏河,靠近山脚那里有拦河坝和抽水泵站,即使没有风调雨顺,这片田也能旱涝保收。
我沿着临河的田埂,一边走一边看,时有乡亲与我打招呼:“乡长,吃晚饭了吗?”
我说:“吃了,你们怎么还不收工呢?”
他们说:“中午太阳大,刚出来不久,现在阴凉,多干一阵子,”
我说:“你们辛苦了!”
他们笑着说:“种田的就这样了。”
这垌田大部分还没有收割,从谷穗的长势判断,今年应该是个丰收年。然而,在这丰收面前,我却有些迷惑不解,因为在这垌田当中,有几块田杂草丛生,没有种下庄稼。去年,因为旱情较严重,我多次走这条田埂,去查看拦水坝和抽水泵站,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今年开春后,因为风雨正常,我就没往这里走,所以不知道失种的情况。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肥沃的田地却丢荒了呢。
为了收割方便,田中早已排干了水。我往回走到一块田边停了下来。田里大概是母女俩吧,正在忙碌着,女儿挥镰割谷,一扎扎谷穗,整齐地摆放在割去稻穗后的禾蔸上;母亲收拾着摆于禾蔸上的谷穗,放置于挑篮中。
我向她们走过去,临近时说道:“大嫂,今年的稻谷长得不错啊?”
正在收拾谷穗的母亲说:“还可以吧。”
“还有钩刀吗?”我问道,手痒痒想重温一下久违的农活。
“钩刀是有,但乡长你干不了这粗活的。”被我称为大嫂的母亲笑着说。
我说:“我过去在家也经常干过这种活的。”
正在割稻的女儿,停下来含笑给我递来她正在用的钩刀。我接过刀后道了一声谢谢,她莞尔离去什么也没说,在不远处的禾蔸上拿回一把钩刀,那把钩刀应该是她母亲刚才用过的。我拿着刀柄尚有小姑娘余温的钩刀,细细端详了一下,这钩刀是十万大山地区农村专门用来割稻谷的一种刀,由木钩和锯齿镰两部分组成。它的一边是木钩,另一边于木柄中间斜插固定着一把锯齿镰,钩长二十公分,柄长四十公分,向前斜插的锯齿镰约为三十公分。
小姑娘来到我旁边,又开始娴熟地舞动钩刀。我也弯着腰,右手握着钩刀向前伸,木钩拢回一扎稻穗,左手向外接抓钩回的稻穗,右手有意识或习惯地稍松动,让锯齿镰下转钩住左手稻穗下的稻秆,然后右臂轻轻一拉,丰收的喜悦就握在手里啦。这样一弯一伸一拢一接一松一转一拉,不断地重复着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扎扎稻穗就或横或竖地排在身后的禾蔸上。由于禾苗长势或各人的力气不同,有时右手只一拉就可以结成一扎,有时要再拉三拉才结成一扎。在乡下好多地方,传统习惯农活由男人耕田犁地挑运,女人主要负责扯秧插田锄地割谷。但我家里人多劳力少,所以,从小到大不分男活女活重活轻活,主要力气所及能干的我都去干,所以对农活比较熟悉。因此,眼下操刀割稻谷还挺顺手,没有生疏的感觉。
“乡长,没想到你还会割稻谷啊。”大嫂来到我附近夸赞道。
“马马虎虎吧。”我答话后也想了解一下丢荒的事,于是问她:“大嫂,那边几块田为什么没种谷呢?”
大嫂说:“有一户人家已搬去县城,去年勉强种了一年,今年就没种了。还有两户人家能干活的都外出打工了,老的小的在家也没办法种呢。”
“那户去了县城的人家,可以把田转给其他人种呐。”我感慨说道。
大嫂说:“地还是他的,他不说话谁敢动啊”
我又说道:“还有其他两户,也可以请人帮一下忙吧?”
大嫂说:“难呐,地不犁耙秧苗不育,也没跟邻里说一声,怎么帮啊?”
“那这两家没有粮食怎么办呐。”我有些担心。
大嫂说:“打工有钱就买呗。”
“如果有工做还好,没工做日子就不好过了。”我感叹说。
“乡长,不用操心,天晚了回吧。”大嫂说着和女儿挑着稻谷回去,我也往乡里走。
晚风习习拂过尚未收割的稻田,空气中散发着新谷的清香。面对丰收我心情还是有些苦楚。全乡农田丢荒现象还是比较严重,除了前面两种情况外,因旱因病因虫因偏僻因缺水而失种的也不少。作为一乡之长,有些情况或许我可以解决,有的我真的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