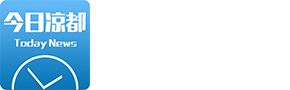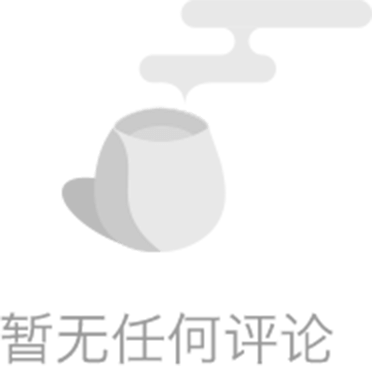秦科
从盘州出发到竹海,大约需要一炷香的时间,转几道弯,爬几道坡,就到了最高处的狗跳崖。狗跳涯占领了众山峰的制高点,空旷,辽阔,适合与命运之间来个了断。每个来到此处的游客,都会无限的放大自己的眼界和格局。哪怕山间的一只蛐蛐,或者虫鸟,也可以目空一切的俯视芸芸众生。率先到这里结束生命的是长工阿海,追赶他的家奴举起屠刀之前,他已将半只脚伸向了悬崖边上,纵身一跃,把泥土砸了一个坑。接着是云竹,她万念俱灰,睡在一片白云上,把自己投放到阿海身旁。白云明显带着暗伤,在风中滴着霓虹的泪,低头的瞬间,已望穿秋水。忠诚的小黑狗,是感动,或许是慈悲,它四脚腾空而起,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在阿海和云竹附近,深陷的脚印像四朵含泪怒放的梅花。我相信,很多恋人曾在这座相思亭下,十指紧扣,借着清风明月海誓山盟。一转身,掉入尘世的烟火,曾经的海枯石烂只是一句美丽的谎言。
从狗跳崖往下走,陡峭,惊险。大部分文友沿着栈道欣赏美景去了,留下驾驶员把车子开到景区的尽头。停好车,我们顺着栈道逆行而上。朱华胜老师说,这片竹海是祖先们留给此地百姓的一笔财富,前人栽竹后人享福。他选定了一处绝美的风景,吆喝着另外几个老师拍照留恋。面带杀气却有菩萨心肠的李永超诗人在这片竹海中行走,他的表情一直是温和的,原来是摄影师拍摄的角度不对引起的误会。李廷华老师每隔五分钟就在林间像喊魂一样的叫我的名字,我挎着笨重的相机赶紧跟上。进入林间,影影绰绰,竹鼠早已掘地三尺,躲在迷宫里准备偷袭某棵竹子的要害。风轻轻地掰开竹叶,天空其实只有巴掌大,飞鸟要想偷窥竹林里的秘密,只能寻找缝隙窜进来。最先来打探消息的是一只红嘴鸟,它掉进了一个小孩设置的圈套中,在竹笼里惊恐的乱撞,另外几只在竹枝上“唧唧啾啾”的叫着。有人猜想,笼子里的鸟定是一只雌的,用它可以勾引另外几只雄的。捕鸟的孩子很老道,他与红嘴鸟玩起“捉放曹”的游戏,旁边支起扑鸟神器,等着鸟儿们自投罗网。后来,在旁人的劝说下,小孩打开笼子,像可怜自己一样的可怜那只红嘴鸟,拎着空空的笼子远去了。
从山顶往下看,最初是一棵,然后是一排,接着是一大片竹子成群结队的穿过村寨,爬满山岗。村庄淹没在翠竹丛林间,若隐若现,蜿蜒的公路像一条麻线,直接延伸到命运的谷底。生活在竹海里的人家,他们把一日三餐和一年四季镶嵌进竹条编成的竹篮,竹箩,囤箩,簸箕和筛子,背着它们到镇上的集市,换回生活的细软,循环往复的日子不断叠加了活着的厚度。小时候,老厂镇有个技艺高超的老篾匠,他编织的箩筐又轻巧又好看。老篾匠去我们村上给人编织箩筐,我蹲在他旁边,看他把一棵棵砍来的竹子破成四半,放上木头钉成的小十字架破竹子,“嘭嘭嘭”的几声脆响,竹子就变成竹块,在几下又变成竹条。他用篾刀横着把篾条破开一小截,用手轻轻地扭弯,三下五除二,篾条变成了细丝,一棵棵竹子在他手里就像吃饭一样轻松自如。老篾匠爱喝酒,打箩筐时候哼小调,高兴时候还会唱山歌。我学他破竹子,只是他把小十字架放在心上,而我是放在手上。我把他扔掉的竹筒织成刷把,带回家给母亲刷锅用。母亲说,篾匠是没有出息的人学的。那些年,似乎带匠字的都矮别人一截,除了篾匠,还有木匠,铁匠,喇叭匠等等。如今,我站在这片竹林里,想起那个老篾匠,当然,也想起《笑傲江湖》里面那个绿竹翁,世人眼拙,看不出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生活奥秘的人。
我们去得不是时候,如果是在春季,几场雨过后,可以见到一种隐花菌类的竹荪。那些红红的竹笋蛋有的已经破“壳”而出,有的已经将白白的“镂空裙”从菌盖向下铺开,犹如一位楚楚动人的美女,衣袂飘飘,翩翩起舞。竹荪味道鲜美,素称“山中之珍”。沿着栈道继续往前走,卢玉兄弟跑错了地方,看见几片破瓦遮住的小房子,他探进头去看过究竟,一股刺鼻的臭味熏得他赶紧缩回来,原来是一间茅房。茅房只有一个进出口,没有门,村里人之前上厕所都是使用暗号,这些失传的暗语早已被“男”和“女”两个字代替了。
老厂镇后来更名为竹海镇,竹海镇的竹根水,清凉甘冽,适合煮酒,名为竹根酒。坐在林间,风起时笑看花落,雪舞时举杯对饮,喝下它,可以醉倒一片森林。在幽深的竹林中穿梭,误入竹缘溪的小桥下,在某个雨打芭蕉的黄昏,看古老的水车转动山水,山与水共清欢,显得不是很寂寞。竹海寺里的晨钟暮鼓,夹着梵音,把高深的偈语写在竹子上。
作者通联:云南省富源县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