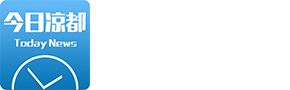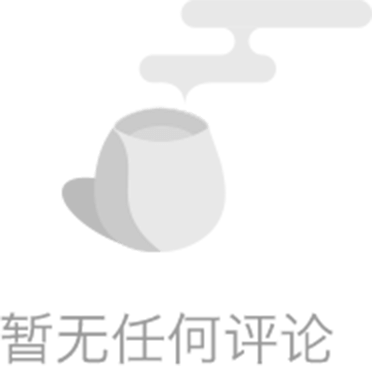远在四川的我,常听父母谈及,水城的羊肉粉如何美味,如何清香,对它的臆想,就如同对父母的思念,一直延续到十二岁那年。
刚到水城时,发现这里羊肉粉馆极多,从黄土坡到场坝,人民路沿线隔上一段便有几家。昆明人开的也好,大方人开的也罢,大都打着“金沙羊肉粉”的招牌,置身其中,会有种到了金沙县城的错觉。
金沙羊肉粉在水城为何有这般影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城的工矿企业在金沙大量招工,许许多多的金沙人加入三线建设的大潮。他们在水城开了第一家羊肉粉店,之后便蔓延开来,水城人对羊肉粉的喜爱便是从那时开始。其中廖家粉馆,就是学生时代我较为熟悉的金沙羊肉粉馆。
它的店面在人民路旁,如今的麒麟公园脚下。
记忆中,柏油路两旁是茂密的梧桐。梧桐叶大、身茂,悉心把馆子揽在羽下,为它遮风挡雨。馆子面积虽不大,仅一间平房,但因当道的地势和出众的手艺却吸引了八方来客。白墙下,小小的木门旁,砖砌着一座与人齐腰,占墙面四分之一的两孔大型灶台。灶的上方与房盖间镶嵌着几块木板,开店门时需一块一块取下,关门时再逐一安上。早取晚关,城里的门面当时都是这样,不像现在的落地玻璃窗那般方便和透亮。
每日清晨,上学的我透过雾霭,远远望见小窗里粗圆的灯泡下,一口特大的铝锅冒着腾腾的热气,好像从不会间断。灶前,满头银丝,红光满面的廖奶奶,将左手那碗冒尖的、粗滚的白米线,准准扣在右手硕大的漏瓢里,后置于开水中,打一个滚儿,捞出,往上一扬,抛掉多余的水份后,继而倒入碗中。再放上一瓢独家秘制的羊肉高汤,舀一勺焦脆的油辣椒,放几许青油油的香菜、葱花,滴上酱油和酸醋,色香味一应俱全,看得人眼馋口酸。奶奶烫粉的姿势,很是娴熟,与兰州拉面师傅潇洒扯拉的动作有一拼。前来吃粉的队伍排了老长,有熟悉的街坊,也有慕名而来的客人。那些先吃的,也不懂克制,仿佛是故意的,呼哧的声音听得人直咽口水。吃到最后,还孩子气地瞅一眼旁边等候的人,再接着稀里哗啦地把碗底的汤喝个精光。
于我们这些外地孩子来说,吃羊肉粉是一种奢侈。家有喜事或考得高分,节俭的父母方会作为奖励给我们买上一碗,姊妹们便深感莫大的幸福。当我终于可以把羊肉粉当早餐消费时,是十多年后的事,其间,“金沙羊肉粉”辉煌已去,真真儿进入“水城羊肉粉”自己的时代。
如今的水城羊肉粉选用散放的本地矮脚黑山羊,这种羊以重、肥为好,羊膻味适中,肉细味鲜。将肉割成几大块,放入大铁锅秘制汤中大火去浮沫,小火慢慢熬制。煮过心后,掌握好软硬度,取出自然冷却隔上一夜,切成大小适中,薄如蝉翼的肉片备用。熬制的原汤清而不浊,鲜而不腥,避腥香料放多则有药味,放少则膻腥味熏人,各家味道是否正宗首先要看这一锅汤的功夫。因锅汤工夫不俗和独特的口感而扬名水城的便有黄土坡的“元坤”,德坞的“向佳”,场坝的“常回头”,“大河明旺”这些羊肉粉品牌。
就拿以“麻”为代表的“向佳”羊肉粉来说吧,1997年,在德坞马姚路口,也就是德坞水库旁,几间石棉瓦房,几张桌凳,便是最初的家当。但它却以羊肉“真”、汤汁“鲜”、口感“纯”,口味“香”而闻名,前来吃粉的人一波儿接一波儿,络绎不绝。如今,经过两代人的努力,老店已迁居,当然仍在德坞那片地界,连锁店也相继开了几家,仍家家门庭若市。
说也奇怪,只要家住水城,无论是在外读书的学子,还是外出旅游的家人,哪怕只离开几日,回到水城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家粉馆,吃上一晚喷香的羊肉粉,方感踏上家乡的土地,思乡之苦可稍许缓解。
当然,水城人喜羊肉粉与此地的海拔及羊肉的功效颇有些关系。水城地处云贵高原,冬日温差较大,人容易受冷。而羊肉性温,冬季吃羊肉,不仅可以增加人体热量,还可促消化。
诚然,“水城羊肉粉”与“水城烙锅”一样,已成为一种文化,成为水城现象。提到水城,人们脑海中不由得会想到它。虽说羊肉粉店的规模、招牌、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不变的却是人们对羊肉粉那份一如既往的热爱,那份解不开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