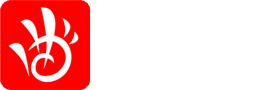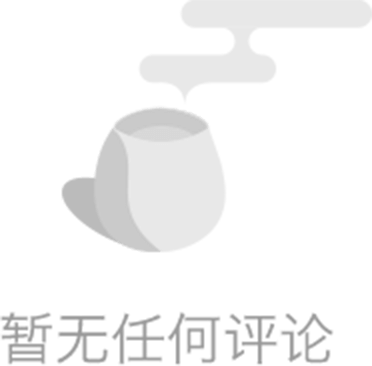在中央红军长征转战滇黔期间,有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英雄部队,这就是被称为“战略骑兵”的中央红军第九军团。1935年4月25日,红九军团由贵州省盘县进至云南省富源县,27日攻占了宣威县城。消息传到会泽,会泽地下党非常振奋,相互联络摩拳擦掌等待红军的到来。4月30日,红九军团进入会泽,在会泽短短的7天时间里,打土豪、开粮仓、壮队伍、强军需,在会泽大地播撒了红色的种子。


7月16日,会泽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从会泽县大井镇出发,沿着红九军团当年的长征足迹,再走长征路,实地感受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1935年4月29日,接中央军委“迅速离开宣威,向川西南披沙(今宁南县披沙镇)前进,准备渡金沙江,如果时间允许并相机袭占会泽”的电令。接到电令的罗炳辉军团长即令作战科长刘雄武率先头部队向灰洞村开进,其余各部进驻宣威县的靖外、渣格、院子田一带。
4月30日,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后勤部长赵镕等的率领下,越过宣威与会泽交界的梨树丫口,进入会泽境内。
中午,大部队在大水、井田一带短暂停留休整、生火煮饭。红九军团的将士们沿井田、色关、仓房、黄梨前进。老百姓听说红军要来,总以为会像国民党军队那样祸害百姓,忙着躲避。面对这些情况,红九军团大力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革命道理、共产党的好政策,激发百姓参与革命的热情。他们在井田坝沈家墙壁上写下“打富济贫”“不交租,不还债”等标语;经过二道箐时,见村民往村外跑,便喊:“老乡不要跑,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不抓兵,不要你们的任何东西。” 他们用高价买面条煮吃,还请去探望他们的老百姓一起吃饭。通过宣传,村民们消除恐惧心理,主动帮助红军。
傍晚,红九军团到达牛栏江边时,正遇江水大涨,无法渡江。同时,国民党为了阻止红军过江西进,命令者海区公所把渡口的所有船只预先坠入江底,没船渡江;国民党军队还在牛栏江边修筑碉堡堵击红军,区长姜香圃又派民团20余人到江边围堵,让红军无法过江。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通过宣传发动,在小湾头渡口,高明刚五兄弟主动捞起木船为红军划渡,红军才开始渡江。
在采访中,高明刚的孙子高顺友告诉记者,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小湾渡口,是他们爷爷辈时候的渡口。高顺友说,当年红军从宣威那边过来,要从江上过去,是爷爷那一辈的老人帮助渡过去的。渡过去之后,红军花钱把船买下沉入江中,免得后面的国民党兵追上他们。
记者在牛栏江的另一个渡口——背锅石渡口采访时,陈礼昌的侄子陈荣正也打开了话匣子,指着江边的路口说,他爸爸告诉他,当年红军长征就是从现在这个地方过江,一个彭姓老人和一个蔡姓老人划了两天,由于船少效率低,就动员老百姓把周边的船集中在一起,用绳子把船连起来,凑了些木板铺在船上面给红军过。陈荣正还告诉记者,这个村子叫塘上,当年红军到这个村子时,陈宝昌就跟着红军到了者海。由于陈宝昌是家里的小儿子,他母亲就叫他哥哥陈甫昌把他追回来,但陈甫昌到了者海受到红军的影响,也没回来,哥俩一起跟随红军长征去了。据说,陈甫昌后来参加战争牺牲了,部队寄了一个证件回来,现在只有一张照片。

陈礼昌是大井镇马鞍村塘上人,家中有兄妹5人,他排行老三。12岁时,被生活所迫,移居者海。他从小就有当兵的念头,心想:“我也要当兵,挎上手枪,在大街上威风凛凛,耀武扬威,不受人欺负。”结果被父母大骂。
5月1日这天,陈礼昌正和几个小伙伴在者海街上玩,忽然看见一支扛着红旗,齐齐整整、威武雄壮的队伍来到者海街。他们很害怕,匆匆忙忙跑进山里躲了起来。但后来他看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不抢、不拿群众的东西,不拉夫、拉马,不拿粮不要钱,买卖公平,对人和气,斗贪官、打土豪。
“这支队伍对穷人这么好,待人特别和气,与以前我们见到的队伍不一样,的确是穷人的队伍,我要参军去。”陈礼昌主意已定,于是避开父母离开了家,偷偷地参加了这支军队,开始了革命生涯。1936年6月,在三十二军二营经教导员赖光武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班长、排长等职。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在一二O师三五九旅718团任团通信参谋、连长、三营副营长。

十四年后,陈礼昌又返回家乡马鞍,组建黄梨游击队并任队长,高举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伟大旗帜,在黄梨、盐塘、木厂等牛栏江一带,带领人民大众翻身闹革命,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会泽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老船工蔡兴发的孙子蔡元贵告诉记者,听他父亲讲,他爷爷和河对面的彭连才两个人划船渡红军过江。
渡牛栏江结束,付船工每人一块大洋;在夜宿地,不论住民房,还是搭棚露宿,都整理清洁;凡是用村民的东西,都归还原物或者按价付钱……鲜艳的红旗、整齐的队伍、严明的纪律,村民感到新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
当晚,在小湾头渡口和背锅石渡口,在当地群众的大力帮助下,天黑以前,红九军团的全部人马顺利渡过牛栏江。大部队在沿江的下寨、马鞍、福桥、坡脚一带宿营,先头部队则越过黄梨树大坡,抵达者海东面的范合落、江坡头、烂泥巴一带宿营。
红军的言行,感动了村民。一批批男女老少沿途沿村送迎整装行军的铁流,一拨又一拨青年尾随队伍前进,有大队人群立于叶家村背后的山顶上,遥送行军的队伍。赵国云、李朝安、徐汝仓、董凤先、孙泽元、陈礼昌、陈宝昌、陈甫昌等29位青年干脆跟上队伍参加了红军,有的走后再无消息,也有的坚持到达陕北后还参加了抗日战争。
在采访中,会泽融媒体中心记者来到陈甫昌的孙子陈国彦家,看到墙上挂着两个相框,其中一个装着一张黑白的老照片,记者好奇地问道:“这张照片是谁的?”陈国彦高兴地介绍道:“这张是我爷爷的,他叫陈甫昌。”接着他指向另一个相框中一张穿军装的老照片说:“这张是我二爷爷的,他叫陈礼昌。他们是一起去参加红军的。后来,从部队寄来我爷爷的证件和这张照片,人没回来,不知道是怎么牺牲的,因为当时信息不发达,没了解情况。新中国成立后,陈礼昌一直在昭通市工作,到1983年去世。”
当时的红军队伍条件艰苦,缺衣少食,装备非常落后,他们身穿灰服、长条、对襟衣,头戴遮凉帽、缎帽、套头,脚穿草鞋,虽服饰各异,但纪律严明,对人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红军长征过程中的一言一行老百姓们看得见,地下党组织也看得见。这是一支真正为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而奋斗的队伍。
在大井镇,曾有村民记得红九军团“手捧滇军,脚踩川军,拖死中央军,吓死乡团兵”的宣传口号。也有红九军团过牛栏江时响彻云霄的口号,“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长官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红九军团经过大井时,处境十分危险,前面有堵截,后面有追兵,还有者海民团、胡所江防中队、兴帮剿匪大队驻扎在黄梨树附近,他们既要赶路,又要对付敌军干扰,实在是不容易。
红军走后两天,国民党湘军李抱冰部队就跟踪而来,有一部分还在大水塘宿营,湘军每到一个地方,就派粮派柴、抢老百姓的东西。路经井田坝时,还在寿佛寺的墙壁上写下“追剿残匪”的标语,到黄梨树时,强迫村民用船、门、木料、方板等架桥,但架桥的工钱,每人仅付一毫钱。红军对百姓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深深打动了劳苦大众,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红九军团渡过牛栏江后,大部队马不停蹄翻山越岭继续前行,先头部队则越过黄梨树大坡抵达者海镇。
(图片提供:李永星、周朝祥、会泽县党史研究室)
曲靖日报特约记者 尹永权 代玉春 夏粉娥 杨梅 通讯员 李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