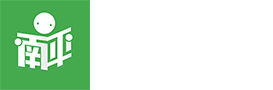我还在家乡生活的时候,村里有一道特殊的风景,就是每一栋房屋的厅堂,至少都有一架纺车。
能够驾驭纺车的,都是属于我叫婆婆辈的人物,她们全都清一色的“三寸金莲”,每一双小小尖尖的布鞋,都像一个翘角的小船模,上面绣着各式各样的花,红红绿绿,各自展现着主人的手艺。婆婆们全都能纺会织,能描会绣,技艺十分精巧。上纺车时,她们个个打扮得齐整,发髻盘得油光发亮。她们端庄地坐在纺车旁,膝上架着一只笸箩,一只小脚踏在纺车轮子的竹踏板上,轻推慢回,把散盘在笸箩中的丝线,卷上纺车的叶轮。
很早的时候,村里很难得有人穿棉布,人们的穿着,就凭着她们的一双巧手。我还小的时候,村里人还把外面买回来的机织棉布叫“洋布”,但大多数人家床上盖的被套、挂的蚊帐,都还是土布缝制的,只是有了染布匠来,家家户户就把织好的土布请匠人去染,也没有什么多样的颜色,除了淀蓝就是藏青。布匹染好,再请裁缝裁剪缝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村里已有了供销合作社,棉布的品种花色也多起来了,什么劳动青、灰卡几、白糙洋,还有其它款式的红布、花布等等,并且后来还出现了“的确良”“的确卡”等化纤产品,但买布还得凭票供应,基本上一个人一年的布票,最多也只能添一套新衣。所以在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初,村里的纺车仍是一道风景,一首古老、优雅的歌。
纺车,仿佛一个时代的划分。我的母亲就不会踩纺车。我的母亲五个姐妹,就从她开始不会踩纺车,村子里也就从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那一代人开始,不会纺线织布。因为她们都是大脚板,轮到要她们缠足的时候,恰好遇上了民国革命,免了她们的皮肉之苦。听说我母亲还差点被缠足,外婆挑好日子要给她缠足,她早早就跑到野外去打猪草,有意错过了时辰,回家无非挨了一次打骂,但她逃过这次劫难,就迎来了政府下令废除妇女缠足。
过去凡被缠了足的女子,基本就免去了户外的劳动。小脚走不动,就窝在家里跟着奶奶或母亲学“女红”,纺线织布、绣花纳鞋,就成了她们的必修课,一直修炼到出嫁为止。“女红”修得好,出嫁也光彩,嫁到一个村庄,人们看她穿在脚上的三寸绣花鞋,就个个“啧啧”称赞。
时代总是在进步的,应该说我母亲她这一辈人,尽管少学了一门纺绣之技,但毕竟免去了终生的缠足之苦,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儿育女的时候,早期婆婆做手工纺织,后来工厂化的生产日新月异,也证明了她们无需学习“女红”。
我在农村成婚那年,“的确良”“的确卡”已经有 了,布票份额也提高了很多,做蚊帐的纱布三寸布票就可买一尺,但我母亲决意不肯买纱布做我的新房蚊帐,说结婚是喜事,不能挂白帐,而且棉纱布的透气性也不如土织布好,拗不过,我只好听从母亲安排。
那年春天,母亲叫我到鱼塘边上去挖了一块地,整了一条厚厚的畦垄,又叫我挑了二桶腐熟的粪便作基肥,母亲就在地里撒上了苎麻种子。没过多久,苎麻苗就密密麻麻地从土里冒了出来,过了一阵子,母亲又仔细地去地里间了苗。由于基肥下得足,那长长的一畦苎麻长得比我还高出半截。快入秋的时候,苎麻成熟,母亲又叫我去把他们割了。母亲叫来我伯婆帮忙,花了一天时间,将苎麻一根根地剥下外皮,绑成二捆放溪水里用石块压住。几天以后,苎麻的表皮就已经腐烂,母亲来到溪边,将它们放石头上,用捣衣板捣了又捣,搓了又搓,苎麻腐烂的肉质表皮就全被洗去,仅剩柔韧光亮的纤维。
晒了两天,两捆苎麻就像摊在晾衣杆上的银丝,一阵微风,飘飘扬扬。苎麻晾干后,母亲就将它们交给了伯婆,那一阵子,除了一日三餐站站锅台煮菜,其它时间都跟着伯婆学着抽丝和接丝,一个多月的工夫,才把一畦的苎麻抽成细丝,并逐根连结起来散盘在笸箩里。
麻丝抽好并连结完后,母亲就再也插不上手了,伯婆就用她的纺车再慢慢地纺成纱锭,之后就在厅堂上架起她的织布机,先细细地布好经线,就凭着手工飞梭,脚踩打梭棒,生生将十几个纱锭变成了一匹宽大的土麻布。
后来,赶巧村里来了个染布匠,母亲花了6角钱将布染成了淀蓝色,再请来我的外公手工裁剪,缝制了一顶宽大的蚊帐,还在帐楣上,镶上了她和父亲用过的那块挂满铜线的帐帘,帐门一牵,琅琅作响。
时间久远了,几次搬家,那顶蚊帐也不知去了何处,连同被时代取缔的婆婆们的纺车,只能被装帧成我的记忆。